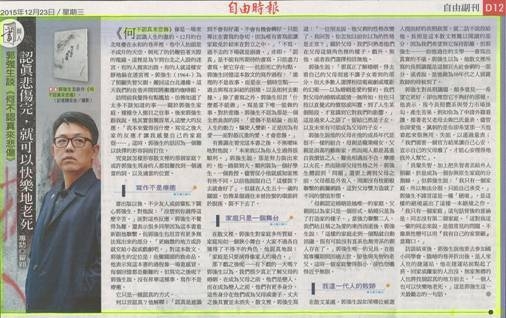解密黃仁勳的領導哲學與魅力,輝達員工回憶:「我永遠忘不了第一次看到他大發雷霆的樣子」
全球第一本黃仁勳授權採訪傳記《黃仁勳傳》,作者提到黃仁勳作為輝達的執行長,他的領導風格充滿矛盾:他一方面嚴厲批評員工,公開展示錯誤以讓其他人汲取教訓;另一方面,他也以情感聯繫員工,甚至在困難時給予無私幫助 ...
全球第一本黃仁勳授權採訪傳記《黃仁勳傳》,作者提到黃仁勳作為輝達的執行長,他的領導風格充滿矛盾:他一方面嚴厲批評員工,公開展示錯誤以讓其他人汲取教訓;另一方面,他也以情感聯繫員工,甚至在困難時給予無私幫助 ...
你是否曾在人際關係中,感到疲憊、委屈或困惑?這本由思維槓桿所撰寫的書,正是一本關於自我探索與情緒覺察的實用指南。作者米克與麥可透過心理學理論與真實經驗,將日常的人際互動轉化為修練自我的機會,帶領讀者一步步釐清內在的需求、拉開情緒界線,找回與自己、與他人連結的自由與自在。

《自由時報》副刊特別專訪郭強生教授,探索悲傷的定義。
專訪◎翟翱
寫作不是療癒
書出版以後,不少友人或前輩私下關心郭強生,對他說:「沒想到你過得這麼辛苦。」面對這些反應,郭強生不覺得為難,還表示很多同學因為這本書重新跟他聯繫。但郭強生也坦言有更多無法寫出來的部分,「更幽微的地方或許就交給小說或戲劇吧。」對這本散文,郭強生的定位是:危難關頭的救命品。他表示寫這本書的過程像一場重感冒,每個回憶都是艱難的。但寫完之後呢?郭強生說,沒有昇華這種事,寫作不是療癒。
它只是一種認真的方式。
何以言認真?他解釋:「認真是意識到不會有好運,不會有機會轉好,只能專注在書寫的急切,因為唯有書寫能讓家庭免於結束在對立之中。」「不寫,過不去的下場就是崩潰。」亦即,「認真」是不能有所期待的書寫,只能盡力書寫,使它存在──抗拒死亡的句點。郭強生回憶這本散文的寫作過程:「處理的不是故事,而是在一個時空點──過去與現在糾結的困境,以及如何去衝撞。」除了書寫之外,郭強生坦言「什麼都不能做」。寫是當下唯一能做的事。對於悲傷,郭強生不認為那是一個全然負面的詞,「悲傷不是結論,而是人生的動力,驅使人變新。正是因為有愛──面對最沉重的愛,才會悲傷。」
有舊識在看完這本書之後,不無曖昧地對他說:「本來我以為你人生過得很順利。」郭強生說,那是努力裝出來的,他一路裝到大,順利裝為一個好學生、一個教授。儘管從小他就感知家裡有些不同。以前他說服自己「這樣裝下去就會好了」,但就在人生五十一歲的關頭,彷彿某個過往未曾拴緊的環節終於脫落,裝不下去了。
摘自《自由時報》【書與人】認真悲傷完,就可以快樂的老死 ──郭強生談《何不認真來悲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