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黃仁勳的領導哲學與魅力,輝達員工回憶:「我永遠忘不了第一次看到他大發雷霆的樣子」
全球第一本黃仁勳授權採訪傳記《黃仁勳傳》,作者提到黃仁勳作為輝達的執行長,他的領導風格充滿矛盾:他一方面嚴厲批評員工,公開展示錯誤以讓其他人汲取教訓;另一方面,他也以情感聯繫員工,甚至在困難時給予無私幫助 ...
全球第一本黃仁勳授權採訪傳記《黃仁勳傳》,作者提到黃仁勳作為輝達的執行長,他的領導風格充滿矛盾:他一方面嚴厲批評員工,公開展示錯誤以讓其他人汲取教訓;另一方面,他也以情感聯繫員工,甚至在困難時給予無私幫助 ...
你是否曾在人際關係中,感到疲憊、委屈或困惑?這本由思維槓桿所撰寫的書,正是一本關於自我探索與情緒覺察的實用指南。作者米克與麥可透過心理學理論與真實經驗,將日常的人際互動轉化為修練自我的機會,帶領讀者一步步釐清內在的需求、拉開情緒界線,找回與自己、與他人連結的自由與自在。

沒有真正挑起照顧父母責任的子女,就算是自己成了家,也還是一個孩子,不算真正長大。

不久前把廚房的流理台換新時,發現了一只我不知竟然還存在的盤子,藏身於一堆鍋碗瓢盆中。
橢圓長型的瓷盤,有三十多公分,最適合拿來盛一尾紅燒魚,或是擺放醃牛肉香腸火腿之類的冷盤。盤子的兩頭畫著杏黃色的花朵與綠葉,我端詳了半天,發現從幼稚園到已老花眼的現在,我仍然無法分辨那上面畫的圖案,究竟是百合還是金針。
但是我對它印象深刻。通常,需要動用到這只大盤的日子,一定是家中有客人來,或是過年過節加菜。原本應該是一整套的餐具,因為還記得幼時曾用過有著同樣花飾的湯匙,約莫是,都已同其他那些碗啊瓢啊全一件件摔壞了,扔了。但是多麼奇怪,這只四十多年前的舊物,竟還毫髮無損地在我們的家中。
最後一次看見它,應該是十五年前。
那是母親在世的最後一個跨年夜,傍晚從花蓮趕回台北,我匆匆去超市買了條黃魚。母親那時已被化療折磨得食不下嚥,但是卻不知為什麼,我當時仍堅定相信,母親最後一定會好起來。
馬上就是二○○二了,我一面為黃魚化霜,一面找出了那只在我們家代表了節慶的大瓷盤,心想著一家三口還是應該一起吃頓應景的晚餐。我幾乎認為,一道紅燒黃魚用這只盤子裝著端上桌,一切都會順利地延續下去。
已經忘了,後來那晚父親為了什麼事與母親鬧脾氣,始終不肯上桌吃飯。母親吃不下,我也沒胃口,剩下大半條沒動過的魚被我全裝進了廚餘桶。我默默洗著碗盤,隱約感覺到,有些什麼我一直倚賴不放手的東西,同時在水龍頭下就這樣一點一點流逝中……
後來那些年,父子二人都成了固定的外食族。我接了系主任兼所長的工作,一週得在花蓮五天,只有週末才能回到台北。父子短暫週末相聚,也都是在外面餐館打發。母親過世後,我再沒有正式動過鍋鏟下廚。頂多燒開水煮把麵,或把打包回來的外食放進電鍋加熱。家中廚房開始成為無聲的記憶,總是那麼乾乾淨淨。
第一個沒有母親的大年初一,中午我和父親來到當時仍叫希爾頓飯店的中餐廳用餐。
父親說,你在紐約念書那些年,家裡就剩兩老,已經不準備什麼年菜了。好在台北有許多館子連除夕都開張,我跟你媽大年初一來希爾頓吃中飯,就算是過年了……
當下眼前出現了我的父母獨坐在餐廳裡的景象,內心酸楚異常。
為什麼之前都沒想過,父母在這樣的日子裡會是怎樣的心情?
是無奈?故作堅強?還是吃驚?怎麼一轉眼,自己已成了餐廳其他客人眼中的孤單老人?會後悔當初沒把子女留在身邊嗎?
‧‧‧
(只剩它一個了。)
十五年後再度捧起那只大瓷盤,宛若與家中某個失散多年的一員又意外重逢。如果盤兒有靈,它又作何感想呢?
是感嘆原本與它成套的家族碗盤,如今都已不再?還是欣慰自己仍在這裡?在當年也許曾摔碎了它兄弟的那個小娃兒、如今已是年過半百的我的手中?
如今,我看到換成我取代了母親,與父親坐在餐廳裡的那個畫面。只有父子二人對坐,也還是淒涼。
彷彿終於理解了,當年還不認為自己年老的父親,為何不再想守著這個殘局。大過年的,應該是跟另一個女人坐在這兒吧?或至少也是跟兒子媳婦孫子一家。怎麼會是跟一個不結婚的兒子在這裡無言相對呢?
等到父親多了同居人,這頓大年初一的午餐也就取消了。
初次離家求學的少年,十年後返家,一開始還以為自己仍是家裡的那個小兒子,時間一到就會聽到有人喊他:「吃飯了!」「起床了!」……結果,一連串迅雷不及掩耳的劇變,還不知如何調適,一回神,他已成了步入半百的老單身。
‧‧‧
一直記得,曾被「萬一父母不在了」這個念頭嚇到不能成眠的那個孩子。
如今,面臨萬一我不在了一個人便無法存活的,是父親。
相信父親曾有過忽然清楚的時刻,意識到了自己的處境,那一刻在他心裡掀起的恐懼,就是自己幼年曾經驗過的恐懼。
父親心裡那個孤立惶恐的孩子,就是我。
在母親與哥哥相繼過世後,這個世上我們只剩下彼此了。
兒時曾經害怕的是,父母會突然過世丟下我一人。如今擔心的卻是,萬一我遺傳了母親與哥哥的癌症基因,自己先走,那怎麼辦?丟下父親一個人在世上,誰來照顧?
‧‧‧
沒有真正挑起照顧父母責任的子女,就算是自己成了家,也還是一個孩子,不算真正長大。因為他們還有父母在包容他們,還可以對父母提出要求,要求他們改變,要求他們公平,心裡還有叛逆,還有不耐,跟一個青少年的身心成熟度相差不遠。
直到獨力照顧老去父母的時候,才會了解沒有什麼公平不公平,才會原諒曾經父母對我們的照顧若有任何疏忽或失手,那是多麼不得已。身為照護者才會了解,我們自己也一直在犯錯,也一直在學習。
對死亡的恐懼,對老化的無知,以及對無常的不能釋懷,能夠幫助我們克服這些障礙的,只有陪伴父母先走過一回。
我們都會很好,總是這樣告訴自己。和父親之間那種互相需要,也重新信任的相依關係,都盡在不言中。
雖然,我總不斷地在跟他說著話。
每當坐在父親身邊陪他「望」著電視,或當他不時就閉目遁去外太空漂流之際,我總會想要努力引起他注意,尋找能夠用簡短字句即可表達,或可與他溝通的話題。
(想起當年,那個聽故事的孩子,總愛對沉沉欲睡開始胡謅情節的父親說:ㄟ你講到哪裡去啦?……)
一如遙遠的當年,此刻,那個情境彷彿又重新上演。
並非父親退化了,而是我多麼幸運又回到了過去,能夠再一次操著簡單的字彙,充滿著期待,對父親呀呀述說著,那些平淡生活裡發生的瑣事。
【書籍資訊】
摘自《我將前往的遠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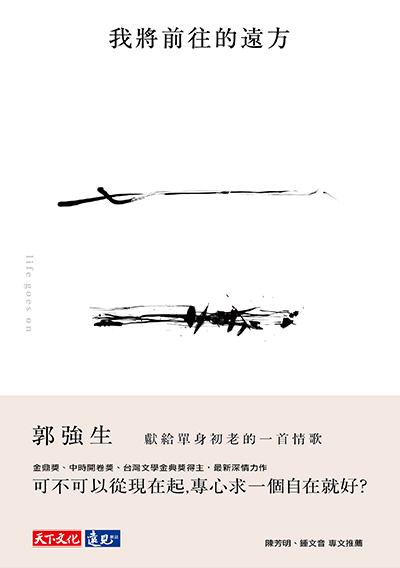
數位編輯整理:陳怡琳,朱玉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