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黃仁勳的領導哲學與魅力,輝達員工回憶:「我永遠忘不了第一次看到他大發雷霆的樣子」
全球第一本黃仁勳授權採訪傳記《黃仁勳傳》,作者提到黃仁勳作為輝達的執行長,他的領導風格充滿矛盾:他一方面嚴厲批評員工,公開展示錯誤以讓其他人汲取教訓;另一方面,他也以情感聯繫員工,甚至在困難時給予無私幫助 ...
全球第一本黃仁勳授權採訪傳記《黃仁勳傳》,作者提到黃仁勳作為輝達的執行長,他的領導風格充滿矛盾:他一方面嚴厲批評員工,公開展示錯誤以讓其他人汲取教訓;另一方面,他也以情感聯繫員工,甚至在困難時給予無私幫助 ...
你是否曾在人際關係中,感到疲憊、委屈或困惑?這本由思維槓桿所撰寫的書,正是一本關於自我探索與情緒覺察的實用指南。作者米克與麥可透過心理學理論與真實經驗,將日常的人際互動轉化為修練自我的機會,帶領讀者一步步釐清內在的需求、拉開情緒界線,找回與自己、與他人連結的自由與自在。

如果坐在書桌前, 想要列出我看過的所有推特、文章和貼文,我能記得的其實少之又少。在網路上閱讀是一項狂亂的活動,壓縮、雜亂,不見得都能消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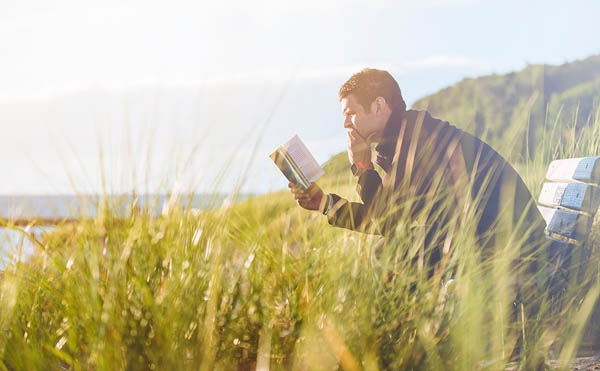
圖片來源:unsplash
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我都掛在網路 上。推特吸引了我一大部分注意力。我很感謝網路提供大量的詳盡資訊,讓我可以追蹤政治、美式足球、詩和新聞八卦。不過,回顧並回想自己一天閱讀過的東西這件事很奇怪。當然,我應該能向我的電腦提出這個問題,找出精確紀錄。但如果我坐在書桌前, 想要列出我看過的所有推特、文章和貼文,我能記得的其實少之又少。在網路上閱讀是一項狂亂的活動,壓縮、雜亂,不見得都能消化。
主動默默閱讀此時開始盛行,而它需要投入。於是讀者成了行動者,作者這時只是一個嚮導,提供各種路徑給他或她那沉默的隱形讀者。如果說中世紀初期的傾聽者/讀者幾乎都是聽一組聲音和聲齊唱基督連禱文,那麼中世紀晚期的「人文」學者就是默默閱讀一整個聲音的世界,每個聲音唱著不同歌曲,而且用許多種 語言……在擺脫口語的束縛許多世代之後,無數的讀者終於能像湯瑪斯.金碧士
(Thomas à Kempis)在《效法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中那樣承認:「我四處尋找快樂,無處尋得,但卻靠一本小書在一方小角落發現了它。」
我們的文化中有一股強烈的衝動,想要逃離這些小角落。我們聽到的是,社會的贏家將是與他人建立關係、相互合作、共同創造及擬定策略的思想家。孩子被教導集體念書,組成團隊執行計畫。職場拆掉牆壁,好讓組織能一體運作。大型科技公司也催促我們加入群眾,它們提供熱門話題,演算法建議我們跟世界其他人看一樣的文章、推特及 貼文。
對話的創造力、向同儕虛心學習的知識潛力、團體合作解決問題的必要性,都是無庸置疑的。然而,這些都不應該取代沉思或隔離的時刻,因為思維在此時能遵循自己的 路徑,達成自己的結論。
我們在自己的小角落、床上、浴缸和小窩閱讀,因為我們知道這些是自己最能思考的地方。我這輩子都在尋找替代地點。我願意在咖啡館和地鐵上閱讀,一心一意、全神貫注。但那始終無法完全奏效。我的思緒擺脫不掉現場的其他人。
當我們專心一致、深入閱讀,就會進入一種外界靜默無聲、近似出神的狀態。頁面上的文字與腦中奔騰抽象概念之間的距離消失無形。如同最初那幾代的靜默讀者那樣, 異端思想在心中來來去去;我們擺脫了知識的束縛。所以我們會習慣性地和自己的書退回私密空間,在那裡不需要擔心社會成規,外界不可能監視我們。因此,我們不能放棄紙本書,即使那些科技公司竭盡全力想達成那種局面。
如果科技公司希望掌控人類生活的所有面向,那紙上閱讀就是它們無法完全整合的少數生活片段之一。
【書籍資訊】
《被壟斷的心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