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黃仁勳的領導哲學與魅力,輝達員工回憶:「我永遠忘不了第一次看到他大發雷霆的樣子」
全球第一本黃仁勳授權採訪傳記《黃仁勳傳》,作者提到黃仁勳作為輝達的執行長,他的領導風格充滿矛盾:他一方面嚴厲批評員工,公開展示錯誤以讓其他人汲取教訓;另一方面,他也以情感聯繫員工,甚至在困難時給予無私幫助 ...
全球第一本黃仁勳授權採訪傳記《黃仁勳傳》,作者提到黃仁勳作為輝達的執行長,他的領導風格充滿矛盾:他一方面嚴厲批評員工,公開展示錯誤以讓其他人汲取教訓;另一方面,他也以情感聯繫員工,甚至在困難時給予無私幫助 ...
你是否曾在人際關係中,感到疲憊、委屈或困惑?這本由思維槓桿所撰寫的書,正是一本關於自我探索與情緒覺察的實用指南。作者米克與麥可透過心理學理論與真實經驗,將日常的人際互動轉化為修練自我的機會,帶領讀者一步步釐清內在的需求、拉開情緒界線,找回與自己、與他人連結的自由與自在。

一名好科學家會不屈不撓為自己的理念原創權辯護,在適當時機勇於批評;但實際上,科學家也常常會急於討好研究領域中的領導人,有時候還屈服在權威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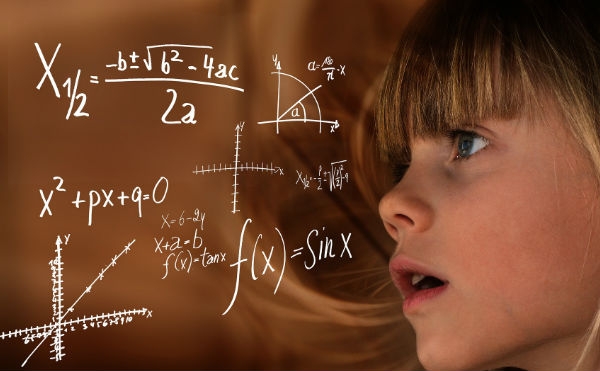
當你聽到「科學可以辦到這些」或「科學無法解決那些問題」時,真正的涵義是科學家能或不能完成某些事情。一名好科學家應是虔誠獻身於科學,有高度的進取心,細心謹慎,坦誠大方,並能相互合作。然而科學家也是人,並不總是能符合這些理想,而來自科學以外的政治、宗教或經費的因素,亦會影響科學家的判斷。
科學界有其獨特的傳統和價值觀,他們由良師、同儕或其他崇敬的偶像那兒,學習到不可作假,不可撒謊,也學習到當競爭對手優先做出發現時,應該將適當的榮耀歸於對手。一名好科學家會不屈不撓為自己的理念原創權辯護,在適當時機勇於批評;但實際上,科學家也常常會急於討好研究領域中的領導人,有時候還屈服在權威之下。
科學家若偽造任何數據,遲早會被發現,那時就是他科學生涯的終結。因此,欺詐在科學界絕不是求生存的選擇。「不一致」可能才是科學家比較常犯的錯誤,而且幾乎沒有人能完全避開這個盲點。
科學家在自己假說和發現中的一些瑕疵,顯然是受困於一廂情願的想法。例如有一位早期研究者發現人類有48條染色體,後續的研究者紛紛證實了這項發現,因為48是他們在觀察時心中預期的數字,一直要到三種不同的新技術問世後,人類具有46條染色體的事實才塵埃落定。
鑑於錯誤和前後不連貫是科學界普遍的現象,科學哲學家巴柏(Karl Popper)在1981年提出了一套職業倫理供科學家參考。
第一,科學界沒有權威的存在,因為科學的論斷遠遠超過任何人的統馭能力,包括所謂的專家。
第二,任何時期,任何一位科學家,都有可能犯錯,我們必須找出錯誤,並分析錯誤的原因,以從中學習,試圖文飾錯誤是不可原諒的罪行。
第三,自省固然重要,有些人可以幫助自己發現、更正錯誤,他們的批評也應該虛心接納;當他人提出質疑時,應予以致謝,他們能讓我們了解自己的盲點。
最後,在指出他人錯誤的同時,也必須警惕自己可能有誤解。
科學家最主要的報酬,就是他在同儕間建立起來的威信。聲譽的建立則來自其科學發現的重要性和他對理念架構的貢獻。為什麼同儕的肯定如此重要呢?為什麼有少數科學家會試圖抹黑同儕或對手呢?科學家做出貢獻後會得到怎樣的回饋呢?科學家彼此之間,和科學家與社會上其他人的關係為何?上述問題在社會學的討論中都曾提及。如同社會學家默頓(Robert Merton)所揭櫫的,現代科學大部分是經由研究團體共同完成的,而合作的聯盟常是服膺相同教條才串聯起來的。儘管科學界中有某種程度的傾軋排擠,但二十世紀後半期,外界所感受到的卻是科學家社群的和諧一致。
能取得一定地位的科學家,往往是頗具企圖心並辛勤工作的人,從來就沒有所謂「朝九晚五」的科學家,許多科學家一天工作將近15到17個小時,或至少在事業生涯的某一階段是如此。然而由他們的傳記可以發現,大部分科學家興趣廣泛,有些甚至是業餘音樂家。但就其他方面而言,科學家也像任何團體一樣,有形形色色的組成份子,有的人外向,有的人內向,有的多產,有的則專注於撰寫少數重要的書籍或論文。我想並沒有一定的個性和性情來刻畫典型的科學家。
【延伸閱讀】
【書籍資訊】
摘自《這就是生物學》

數位編輯整理:徐仕美,朱玉瑩
Photo:Pixabay,CC0 Licens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