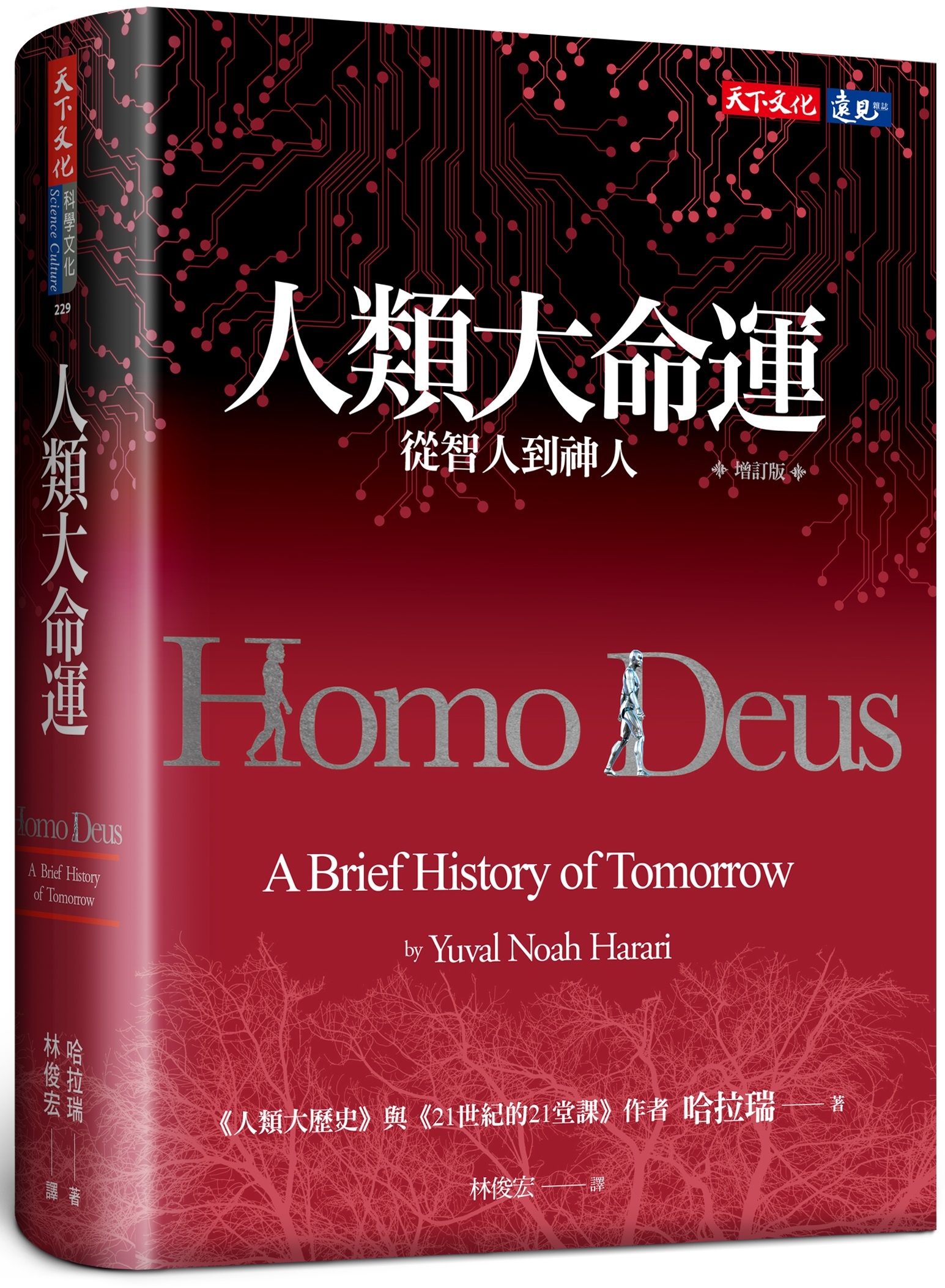解密黃仁勳的領導哲學與魅力,輝達員工回憶:「我永遠忘不了第一次看到他大發雷霆的樣子」
全球第一本黃仁勳授權採訪傳記《黃仁勳傳》,作者提到黃仁勳作為輝達的執行長,他的領導風格充滿矛盾:他一方面嚴厲批評員工,公開展示錯誤以讓其他人汲取教訓;另一方面,他也以情感聯繫員工,甚至在困難時給予無私幫助 ...
全球第一本黃仁勳授權採訪傳記《黃仁勳傳》,作者提到黃仁勳作為輝達的執行長,他的領導風格充滿矛盾:他一方面嚴厲批評員工,公開展示錯誤以讓其他人汲取教訓;另一方面,他也以情感聯繫員工,甚至在困難時給予無私幫助 ...
你是否曾在人際關係中,感到疲憊、委屈或困惑?這本由思維槓桿所撰寫的書,正是一本關於自我探索與情緒覺察的實用指南。作者米克與麥可透過心理學理論與真實經驗,將日常的人際互動轉化為修練自我的機會,帶領讀者一步步釐清內在的需求、拉開情緒界線,找回與自己、與他人連結的自由與自在。

把未來人類的希望,放在「假設未來的科學家能有些現今不可知、卻能拯救地球的發現」上,這種想法真的理性嗎?

究竟科學能否永遠拯救經濟免於冰封、地球免於沸騰,實在沒人說得準。而且,由於腳步不斷加快,能夠犯錯的空間也不斷縮小。以前可能只要一個世紀發明出一項神奇的產品,便已足夠,但現在可能每兩年就得出現一項奇蹟。
我們也該思考,生態末日對於不同的人類階級,又有什麼樣的不同後果。歷史從無正義。每當災難發生,就算這場悲劇根本就是由富人所引起,但窮人受到的苦難幾乎總是遠遠高於富人。
在乾旱的非洲國家,全球暖化已經開始影響窮人的生活,這些人受影響的程度遠比富裕的西方人來得高。矛盾的是,科學的力量愈大,反而可能愈危險;原因就在於這讓富人自鳴得意。
以溫室氣體的排放為例。大多數學者和愈來愈多的政治家,已經開始體認到全球暖化的現實和危險程度,但也僅止於體認,而未有任何實際作為,未能真正改變我們的行事做法。
對於全球暖化,我們談得很多,但到了實際作為,人類卻不願為了制止這場災難,而真正在經濟、社會或政治上有所犧牲。2000年到2010年間,溫室氣體排放量非但完全沒有減少,反而還以每年2.2%的速度成長;過去在1970年到2000年間,年成長率僅為1.3%。1997年協議減排溫室氣體的〈京都議定書〉,目標只是減緩、而非阻止全球暖化,但美國這個全球第一大汙染者卻拒絕簽署,也全未嘗試大幅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惟恐有礙經濟成長。
2015年12月,〈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訂出了較遠大的目標:在2100年以前,追求全球平均溫度升幅要低於1.5 C(以工業革命前的全球平均氣溫為準)。然而,有許多為了達成這項目標所必要的痛苦措施,卻都被輕描淡寫的延遲到2030年、甚至是二十一世紀的下半葉,其實也就是把燙手山芋丟給下一代。目前的主政者一派貌似環保,只想收割立即的政治利益,卻把減少排放(也就會減緩成長)的重大政治代價,留給未來的主政者。
有太多的政客和選民認為,只要經濟繼續成長,科學家和工程師永遠都能拯救我們免於面對末日。談到氣候變遷的問題,「成長」的真正信徒還不只是希望奇蹟發生,而是認為奇蹟的出現是理所當然。
把未來人類的希望,放在「假設未來的科學家能有些現今不可知、卻能拯救地球的發現」上,這種想法真的理性嗎?目前讓整個世界運作的多數總統、部長和執行長,都是非常理性的人。但是為什麼他們願意下這樣的賭注?或許是因為,他們覺得賭的不會是自己個人的未來。就算情況極度惡化,科學再也無法阻擋洪水襲來,工程師仍然能夠為上層階級,打造出一艘高科技的挪亞方舟,至於其他幾十億人,就隨波而去吧。
這種對於高科技方舟的信念,正是對人類未來及整個生態系的最大威脅之一。如果有人一心相信自己死後能上天堂,就不該把核武交到這種人手中;出於同樣理由,要決定全球生態議題時,也不該交給相信這種高科技方舟的人。
窮人又是怎麼回事?他們為什麼不抗議?畢竟萬一洪水真的來臨,將是窮人擔起所有代價。然而,如果經濟停滯,窮人也是首當其衝。在資本主義世界裡,窮人的生活唯有在經濟成長時,才可能有所改善。因此,如果得要放慢當下的經濟成長,以求減少未來的生態威脅,並不太可能得到他們的支持。保護環境是個好主意,但如果有人連房租都交不出來,對於沒錢的恐懼,就會遠遠高過對冰帽融化的擔心。
【書籍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