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黃仁勳的領導哲學與魅力,輝達員工回憶:「我永遠忘不了第一次看到他大發雷霆的樣子」
全球第一本黃仁勳授權採訪傳記《黃仁勳傳》,作者提到黃仁勳作為輝達的執行長,他的領導風格充滿矛盾:他一方面嚴厲批評員工,公開展示錯誤以讓其他人汲取教訓;另一方面,他也以情感聯繫員工,甚至在困難時給予無私幫助 ...
全球第一本黃仁勳授權採訪傳記《黃仁勳傳》,作者提到黃仁勳作為輝達的執行長,他的領導風格充滿矛盾:他一方面嚴厲批評員工,公開展示錯誤以讓其他人汲取教訓;另一方面,他也以情感聯繫員工,甚至在困難時給予無私幫助 ...
你是否曾在人際關係中,感到疲憊、委屈或困惑?這本由思維槓桿所撰寫的書,正是一本關於自我探索與情緒覺察的實用指南。作者米克與麥可透過心理學理論與真實經驗,將日常的人際互動轉化為修練自我的機會,帶領讀者一步步釐清內在的需求、拉開情緒界線,找回與自己、與他人連結的自由與自在。

她應該要當老師,全心全意投入這份一直以來很適合她的工作嗎?還是她應該要挑戰自我,到科技產業找工作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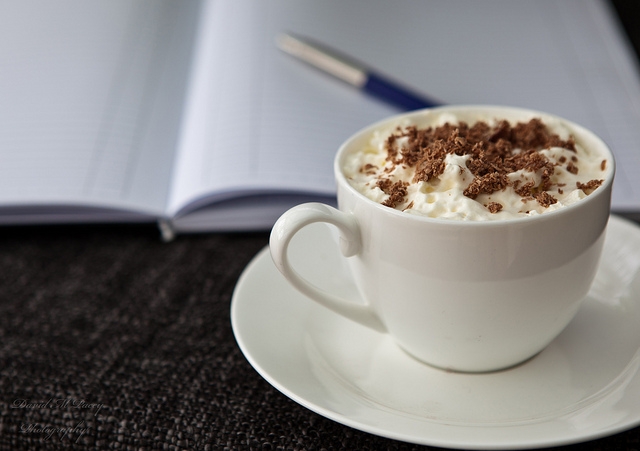
極度內向
瑪莉莎.梅爾出生於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十日。母親瑪格麗特.梅爾(Margaret Mayer)
是美術老師兼家庭主婦,父親麥可.梅爾(Michael Mayer)是環境工程師。
瑪莉莎在威斯康辛州的沃索長大,她還有個運動健將弟弟梅森.梅爾(Mason
Mayer)。她們家算是一般中產階級家庭。
高中時期,瑪莉莎的穿衣風格是T恤、毛衣以及牛仔褲,質料不錯,但不怎麼起眼。就算瑪莉莎在眾人前一直表現出色,但她的同儕並不認為她特別外向。在學生時代,同學們不會覺得她以後會成為總裁。
沃索西高中的課表制度不是傳統的節次,而是把一整天分成每二十分鐘為單位的時段。一節課會持續四十分鐘或一個小時。也就是說,每天都會有數次長達二十分鐘的下課時段。大多數高年級生會利用這段時間,聚集在學校的公共空間,和朋友聊天、吃東西。瑪莉莎則不然。瑪莉莎這種人會走到公共空間,到餐廳或販賣機找點東西吃,然後就到圖書館或科學實驗室去讀書。她不願坐在那邊聊二十分鐘的天。
在瑪莉莎的成長階段,她跟同儕並沒有很親近。童年時期的瑪莉莎大多跟著能夠帶給她成長及引導的大人相處:例如教練、老師、輔導員和指導員。
或許因為她總是跟在老師、輔導員、教練身邊,瑪莉莎從小開始,言行舉止就像老師。瑪莉莎小時候的鋼琴老師瓊安.貝克曼(Joanne Beckman),記得她有一點跟其他小孩
非常不一樣:瑪莉莎經常「觀察別人」,好了解別人為什麼要做某件事。
「很多那個年紀的孩子只對自己有興趣,」貝克曼說:「她則是在觀察別人。」
高中時,瑪莉莎覺得站在教室前對同學講話,對她來說比較自在。她在每個參加的社團
都擔任領導者角色。她擔任西班牙語社社長、同青社總務以及辯論隊的隊長。
一九九三年,瑪莉莎申請的十所大學全錄取她,其中包含哈佛、耶魯、杜克和西北大學。為了決定要去哪一所大學,瑪莉莎開了一個試算表檔案,考慮每間大學的可變因素。
她選擇史丹福大學。她想成為腦科醫生,這一行很適合聰明但內向的人。
一九九四年瑪莉莎上史丹福前的暑假,她開始問自己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會在大學和之後的人生一路引導著她。
祖恩會怎麼想呢?
那年暑假,瑪莉莎參加了在西維吉尼亞州舉辦的全國青少年科學營。那是個書呆子的天堂。想像一下,樹蔭遮蔽的小木屋裡竟然是科學實驗室。瑪莉莎特別喜歡某個實驗,就是把水和玉米粉混在一起,變成濕濕糊糊、似乎可以對抗地心引力的物質。
有一天,耶魯的博士後研究員阮祖恩(Zune Nguyen)來營隊擔任客座講師,他用謎題
和腦力激盪遊戲讓在場的聰明孩子目瞪口呆。連續好幾天,學員都還是一直談論著他的課。
最後,瑪莉莎的輔導員覺得受夠了。
「你們要知道,你們都搞錯重點了。」輔導員對瑪莉莎和其他學員說道:「重點不是祖恩知道什麼,而是祖恩如何思考。」
輔導員說阮祖恩之所以厲害,並不是他的知識,而是他看待世界的方法,以及如何思考問題。輔導員說阮祖恩最了不起的是,即使你把他放在完全陌生的環境,或是丟給他一個全新的問題,他都能在幾分鐘之內,直搗問題的核心、發表正確的看法。
從那一刻起,「重點不是祖恩知道什麼,而是祖恩如何思考」這句話,就留在瑪莉莎的腦海裡,成了她的人生指導方針。
那年秋天,瑪莉莎進入史丹福,開始修習醫學院預備課程,計劃未來要行醫。但是大一快結束時,她對醫科已經興趣全無。我只是在做記憶卡練習嘛,她想。很簡單,太簡單了。全部記熟就好了。
瑪莉莎心目中理想的科系,要能訓練她批判性思考的能力,讓她能善於解決問題。她也想要研究人類如何思考、如何推理、如何表達。她腦中有個聲音叨叨不休:重點不是祖恩知道什麼,而是祖恩如何思考。
瑪莉莎開始回應她腦中的聲音,找到能幫助她學習如何思考的一門課程,也就是資訊工程的入門課: CS105。學期中,瑪莉莎為了加分,參加了班級內部的設計比賽。她設計出一個以璀璨煙火為主題的螢幕保護程式。在三百人的班級中,她的作品排名第二。這個設計實在優秀,讓CS105課程的教授艾瑞克.羅伯茲(Eric Roberts)在稍做修改後,便把這個螢幕保護程式當成之後幾年的作業。
羅伯茲教授對於瑪莉莎的煙火作業相當驚豔,於是邀請她和其他幾個表現頂尖的學生到他家晚餐。瑪莉莎一向與老師關係很好,羅伯茲教授亦成為瑪莉莎的良師益友。
瑪莉莎也找到她想修讀的科系。
瑪莉莎選擇符號系統學,這門綜合學科包含語言學、哲學、認知心理學和資訊工程等課程。
符號系統學是史丹福的熱門科系。除了瑪莉莎之外,其他校友包含蘋果iOS程式前資深副總裁史考特.福斯托(Scott Forstall),還有Instagram的共同創辦人麥可.克瑞格(Mike Krieger)等。
瑪莉莎的教學天分在修「原理160A」這門課時表露無遺。這門課是對未來要主修符號系統學的學生來說,是要求嚴格的「刷人」課程(weed-out course)。在「原理160A」這門課期間,學生必須分成六組左右的研究小組,每組都有各自的作業。瑪莉莎那組和大家一樣,也都等到交作業前一天才開始動手。所以在史丹福的那個學期,對瑪莉莎以及「原理160A」的同組成員來說,熬夜是家常便飯。在小組討論的時候,組內成員會聊個不停,開始拖慢進度,瑪莉莎總是率先發聲:「好了,回到正題,趕快把作業完成。」
她仍然是指揮者的角色,以一貫認真的態度,分配組員的工作。但對功課以外的事情,她很內向,甚至有點孤僻。
多年後,瑪莉莎這樣矛盾的個性組合─樂於像老師那般權威和標準高,不願和同儕發展私人交情,將會給她帶來麻煩。
她在符號系統學系唸到高年級時,接到了「授課邀請」。她很自然的愛上了。
羅伯茲教授監督她的授課。瑪莉莎在春季班的授課結束後,羅伯茲給她的學生做了份問卷調查,結果出乎意料:學生喜歡她,即使她有時候講話速度「飆到每分鐘一英哩」。
羅伯茲教授詢問瑪莉莎是否有意願在暑假時待在史丹福,教另一班學生。瑪莉莎欣然答應羅伯茲的邀約。
瑪莉莎在剩下的史丹福大學時光都表現優異。拿到學士學位後,她繼續待在史丹福攻讀資訊工程碩士,專長為人工智慧。
當研究生日子接近尾聲,瑪莉莎的教學名聲也逐漸傳開。
她很快面臨一個抉擇。
她應該要當老師,全心全意投入這份一直以來很適合她的工作嗎?
還是她應該要挑戰自我,到科技產業找工作呢?
若有人問起瑪莉莎,為什麼拿到史丹福符號系統碩士後會進谷歌工作,瑪莉莎喜歡以「蘿拉.貝克曼(Laura Beckman)的故事」回答。這是她中學時代鋼琴老師瓊安.貝克曼的女兒的故事。
瑪莉莎說起這故事:「蘿拉在高二時候參加排球隊甄選。選拔賽最後,她面臨一個困難的抉擇:要在一軍當板凳球員,還是加入可上場的二軍?」
「大部分人面臨這類的抉擇時,會選擇出場比賽,所以加入二軍。蘿拉卻反其道而行。她選擇待在一軍,坐了一整季的板凳。」
「但之後美妙的事發生了。高三時她參加選拔賽,成為一軍的參賽者,而二軍去年的所有參賽者,在高三時坐了一整年的板凳。」
「我記得曾問她:『你怎麼知道要選一軍?』」
「她說:『我只知道,如果我每天跟比較優秀的球員練習,即使我沒有機會上場參賽,我都能變成更好的球員。』」
瑪莉莎故事的寓意是:讓自己身處優秀的人之中,他們會激發你的成長。
「我想要找到聰明的人並身處其中,所以我來到谷歌,」她說。
這是瑪莉莎加入谷歌的主因。
但她差點錯過這個機會。
瑪莉莎在史丹福的最後一年時,四月中某個星期五她坐在電腦前,邊吃義大利麵邊讀電子郵件。她已經得到十二份工作錄取通知,不想再有錄用通知來加重她選擇的難度。所以當收件匣中又冒出一封人力仲介的工作介紹時,她直接按下鍵盤上的刪除鍵。
只是她沒刪到。
瑪莉莎沒按到刪除鍵,反而誤按空白鍵。信件於是打開。
信件的主旨寫著:「想到谷歌工作嗎?」
瑪莉莎讀著電子郵件,想起之前和艾瑞克.羅伯茲教授的一席談話。去年秋季,羅伯茲聽著瑪莉莎談到她發明的推薦引擎,告訴瑪莉莎應該去會會兩位也在做類似東西的博士生。他們就是謝爾蓋.布林和賴瑞.佩吉。
意識到這封原本她想刪掉的電郵是布林和佩吉的新創公司發來的,於是瑪莉莎回信說她想面試。她得到跟谷歌工程師克雷格.西爾弗斯坦(Craig Silverstein)面試的機會。西爾弗斯坦的聰明才智讓瑪莉莎驚艷。用蘿拉.貝克曼的排球故事比喻,西爾弗斯坦就是那優秀的一軍球員。
谷歌給了瑪莉莎一份工作,正確來說,是實習生工作。
她並沒有馬上答應。她已經得到麥肯錫管理顧問公司(McKinsey)的好工作。在那裡,她的顧客都會是矽谷的公司,她會學到很多,那會是個穩定的工作。
相較之下,選擇谷歌風險高很多。
瑪莉莎決定研究一下風險到底有多高。
她查了和谷歌差不多狀況的新創公司歷史資料,運算龐大的數據,最後得到了一個數
字,代表谷歌可能成功的機率。
她估計,谷歌有百分之九十八的機率會徹底失敗。
但她還是義無反顧的衝了。
摘自《偏執的勇氣》
Photo:david pacey, CC Licens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