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黃仁勳的領導哲學與魅力,輝達員工回憶:「我永遠忘不了第一次看到他大發雷霆的樣子」
全球第一本黃仁勳授權採訪傳記《黃仁勳傳》,作者提到黃仁勳作為輝達的執行長,他的領導風格充滿矛盾:他一方面嚴厲批評員工,公開展示錯誤以讓其他人汲取教訓;另一方面,他也以情感聯繫員工,甚至在困難時給予無私幫助 ...
全球第一本黃仁勳授權採訪傳記《黃仁勳傳》,作者提到黃仁勳作為輝達的執行長,他的領導風格充滿矛盾:他一方面嚴厲批評員工,公開展示錯誤以讓其他人汲取教訓;另一方面,他也以情感聯繫員工,甚至在困難時給予無私幫助 ...
你是否曾在人際關係中,感到疲憊、委屈或困惑?這本由思維槓桿所撰寫的書,正是一本關於自我探索與情緒覺察的實用指南。作者米克與麥可透過心理學理論與真實經驗,將日常的人際互動轉化為修練自我的機會,帶領讀者一步步釐清內在的需求、拉開情緒界線,找回與自己、與他人連結的自由與自在。

當我們被一道需要洞見的問題給困住,而且很想要解開它;在這種情況下,分心並不是障礙,它反倒是寶貴的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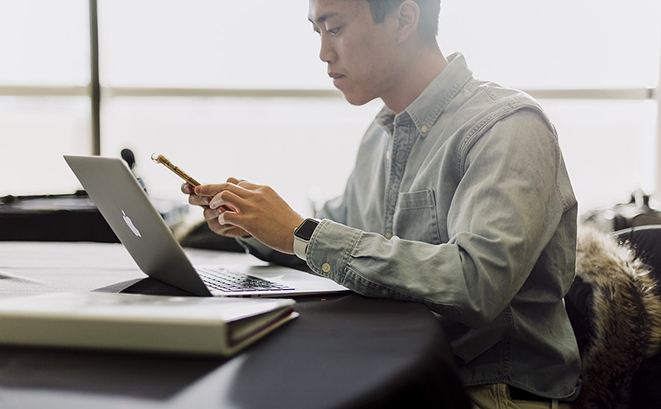
圖片來源:unsplash
醞釀期(incubation):始於你把問題擺到一邊的時候。對於亥姆霍茲來說,醞釀期是從他放棄手上的工作,到樹林裡散步,故意不去想工作的時候開始的。至於對其他人來說,華勒士發現,醞釀期可能發生在夜裡,或是用餐時間,或是與朋友外出的時候。
華勒士知道,腦袋裡的某些祕密策劃,顯然就是發生在這段停工期。這段醞釀期具有很關鍵的重要性。華勒士是心理學家,可不是讀心術專家,但他還是放膽說出他的猜測:「某種內部的心智過程,」他寫道:「在進行新資訊與舊資訊的結合。一種內部的資訊重整,似乎是在當事人並未直接察覺的情況下,自動自發的進行。」
那就是說,腦袋會利用你下線時間鑽研那道難題,繞著它已經掌握到的片段知識打轉,並陸續添加一些它剛開始沒想到可以運用的後備資訊。
想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們不妨舉一個週末動手修東西的例子。譬如說,你打算把一組壞掉的門鎖換成新的。看起來滿簡單的,但問題來了:新的鎖扣板若安裝在門框原來的凹槽,門鎖的鎖舌與鎖扣板上的鎖舌孔無法對齊。
你不想要挖新的凹槽,那會破壞門框;你弄來弄去,就是弄不出個結果。你投降了,放下工作吃飯去,然後突然間……嘿,等一下,我為什麼不使用舊的鎖扣板,只更換門鎖和鎖舌?你原本已把舊鎖扣板丟掉,突然間想起它還在垃圾桶裡。
至少這就是大概的想法,而且在華勒士的認知裡,腦袋裡的祕密策劃包括好幾個成分。一個是潛意識,我們都沒有意識到潛意識的發生。另一個成分是問題(例如,我在學校演講的鉛筆問題)裡面包藏的要件,會被一再組合、拆解,然後再組合。
(擷取自本書第150~151頁)
希奧和歐莫羅將醞釀期分成三種類型:一種是放鬆,例如躺在沙發上聽音樂;另一種是輕活動,例如上網瀏覽;第三種是高度專注的活動,像是寫一篇短文或是埋首另一份家庭作業。
對於數學與空間問題而言,例如鉛筆問題,以上三種活動都可以讓人受惠;你選擇哪一種,似乎並沒有差別。但是對於文字問題,例如RAT謎題或是回文字謎,帶有輕活動的暫停,像是打電玩、單人牌戲、看電視,似乎最有用。
希奧和歐莫羅發現,長的醞釀期勝過短的醞釀期,雖說這裡的「長」是指大約二十分鐘,短是指約莫五分鐘—這麼狹窄的範圍純粹是由研究者隨意決定的。此外,他們也強調,除非人們真正陷入僵局,否則不能從醞釀期的暫停當中獲益。
他們對「僵局」的定義並不精確,但我們大部分人都知道小小的障礙和一堵磚牆之間的差別。重要的是:你如果太快停工來打電動,將一無所獲。
什麼時候應該分心?
將來科學家也不太可能明確指出,對於哪些種類的問題,醞釀期要多長。事實上,醞釀期會因為我們是什麼樣的人,以及我們工作的方式,而有所不同。
沒關係,反正我們能夠藉由嘗試不同的醞釀期長度和活動,來發掘怎樣的醞釀期對我們最有效。反正我們大部分人早就試過暫時拋開已經撞牆了的解題任務,跑去看電視、或是上臉書、或是打電話給朋友;只是我們暫停了工作的時候,心裡多少充滿了罪惡感。
然而,洞見科學卻告訴我們,罪惡感完全是沒必要的,許多這類型的暫停能在我們被困住時,幫助我們解脫。
當我被困住時,可能會到街角去走走,或是戴上耳機大聲聽音樂,或是在走廊上尋找有沒有人可以聽我抱怨。這要看我當時有多少時間而定。不過,在多數情況下,我發覺第三個選項對我最有效。我發完自己的牢騷,活力大增,大約二十分鐘後,走回去,就會發現我腦袋裡的那個結,不管是哪一種結,有一點兒鬆開了。
希奧和歐莫羅的後設分析研究,徹底顛覆了人們對社群媒體和讓人分心的電玩的那種「詭異的歇斯底里」。那種「數位產品會侵蝕我們的思考能力」的恐懼,根本是用錯地方了。
當然,如果我們是把半個鐘頭的讀書時間,拿來上臉書或看電視,確實不應該;或是在聽一場演講、或上音樂課時,心不在焉確實會妨礙我們需要持續專心的學習活動。但是,當我們被一道需要洞見的問題給困住,而且很想要解開它;在這種情況下,分心並不是障礙,它反倒是寶貴的武器。
(擷取自本書第166~168頁)
【書籍資訊】
《最強大腦學習法》
出版日期:2020.08.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