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黃仁勳的領導哲學與魅力,輝達員工回憶:「我永遠忘不了第一次看到他大發雷霆的樣子」
全球第一本黃仁勳授權採訪傳記《黃仁勳傳》,作者提到黃仁勳作為輝達的執行長,他的領導風格充滿矛盾:他一方面嚴厲批評員工,公開展示錯誤以讓其他人汲取教訓;另一方面,他也以情感聯繫員工,甚至在困難時給予無私幫助 ...
全球第一本黃仁勳授權採訪傳記《黃仁勳傳》,作者提到黃仁勳作為輝達的執行長,他的領導風格充滿矛盾:他一方面嚴厲批評員工,公開展示錯誤以讓其他人汲取教訓;另一方面,他也以情感聯繫員工,甚至在困難時給予無私幫助 ...
你是否曾在人際關係中,感到疲憊、委屈或困惑?這本由思維槓桿所撰寫的書,正是一本關於自我探索與情緒覺察的實用指南。作者米克與麥可透過心理學理論與真實經驗,將日常的人際互動轉化為修練自我的機會,帶領讀者一步步釐清內在的需求、拉開情緒界線,找回與自己、與他人連結的自由與自在。

在廚房辛勤耕耘的人,總在餐桌採收豐美的果實。那些付出會結成親族之情、友誼的芳香與質感的生活,撫平人心,增進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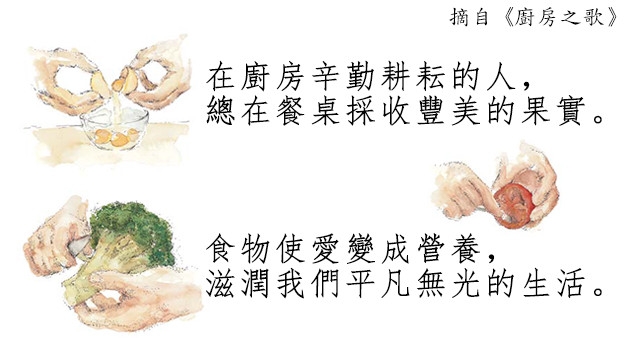
十歲那年,我對廚事與烹飪的異想開始不再仰賴遊戲家家酒了,我真的常常可以在家中的廚房昏天暗地的玩將起來。那年我上小四,家中的哥哥姐姐都離家到遠地住讀。爸媽工作很忙,陪伴我的是《讀者文摘》、《今日世界》與手足離去後的孤獨。我開始在家裡那個大廚房裡,以一個孩子的心思庖製食物點心。一方面幫母親處理家事、一方面驅走時時襲上心頭的寂寞。那個非常柔弱內向的十歲女孩,因為在廚房裡忙碌著,在回想中就不再只是形單影隻的孤寂身影。
父親學的是化學,所以討論我那小小的廚事習作時,他總是給我自由的預設與科學的解釋。母親雖然打理工廠工作繁重,但她一定十分心疼小小的我少了兄姐的陪伴,所以一有空就盡可能與我同讀日文書中那些美好的生活圖片。又為我在家常的餐食準備中,講解許多烹飪的要訣與樂趣。我還記得,第一次在沒有媽媽的協助下做洋菜凍,小身影興奮地奔走在爐火與冰箱之間,計數份量,觀察凝凍的狀況,想起來是十分符合科學實驗精神的呢!
孤獨使我比其他孩子多了許多自我摸索與探尋生活的機會,父母的知識與關懷更使我在探索的過程中有友亦有師。我不是完全被教導的指令灌溉長大的,也不是完全靠自己憑空摸索、繞遠路去體驗生活。我只是快樂地跟著生活的軌道、吸收別人給我的智慧,邁步向前。就像一個完整的廚房經驗,「真實」而且「每天運作」。
童年的廚事經驗使我深刻體認,廚房不只可以庖製出美食,餵飽一個人的「味」與「胃」;廚房更是想像力的實驗室與快樂的製造所。在那裡,許多虛幻的辭彙可以變成具象的物品與真實的感覺,如果這不是魔幻之地,我真不知道哪裡才能被如此呼喚?
我從喜歡烹飪而愛上閱讀食譜。華特·班哲明說:「閱讀使我們成為移民」,對我的食譜閱讀來說,那的確是個完整的形容。我從一本本食譜中窺探別人的廚事心情,跨過食材與風土人情的國界,流連在味與胃的區間。動手炊煮文字化的料理,可以讓一分分陌生的異國之感從熱氣中蒸散掉,繼而品嚐它被描述的美味是否真切。幾十年中,一本本食譜不斷往我的書架上佔據領地,正襟危坐研究食譜,也成了我生活中一件重要的活動。「煮字」不是用來療饑,那些天花亂墜的美麗辭彙經過烹調後,到底還能不能算是美味,成了我最感興趣的問題。當然,因為動手多了,文字就無法再輕易愚弄我,而我也更知道,如果要動筆分享料理的精神時,文字所承載的情感只能跟適當的調味料一樣多,才不會使享用的人感到膩味失真。
在廚房辛勤耕耘的人,總在餐桌採收豐美的果實。那些付出會結成親族之情、友誼的芳香與質感的生活,不一定要奇珍異饈也能撫平人心,增進情感。食物是愛,至少,食物使愛變成營養,滋潤我們以為平凡無光的生活。
十幾年前,我隨著家庭在幾個國家移動,異國廚房裡的烹調大事,不是只為吸收新知美味,更為傳遞思鄉之情與穩定變動生活中的不安。「小朋友!擺餐桌!」是一天當中我自認最悅耳動聽的發號施令。從廚房走到餐廳,看到那些一直陪伴著我們的各種餐具以無邊的樂趣被擺放在餐墊上時,我不再覺得自己是一個遠望當歸的異鄉人。在祝福一餐、傳遞食物當中,我的廚房之歌以愉快的顫音撫慰家中每一分或許曾經感到飄零的心情。
我很幸運,在廚房設備還非常簡陋的年代就開始親近廚事,這使我深刻地感受到食物、烹調與生活之間最本質的關係,也使我能夠在無論多麼簡約的設備下,都不減做一餐好飯菜的期待與決心。快樂的生活是自己動手創造的,千萬不要被環境中的物質條件所框限。如果沒有食物調理機,可以用傳統打蛋器;如果沒有打蛋器,綁一束筷子也可以取而代之。幾千年來,美味都是渴望、創意與行動的合體。
說得一口好菜,在我幼時那個務實的年代還不是一種時尚,但做得一手好菜,卻無論在哪一種日子中都會帶來真正的愉快。所以,我總是悠然地在廚房裡輕哼快樂曲調。那些生活中的歌,是「手」與「心」的合聲;是母親與我、我與女兒家事傳承的重唱。
摘自《廚房之歌》
